老龄化不仅带来了对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的重大压力,也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管理、法律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针对孤寡老人、无保护老人和失独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监护问题。
随着社会结构和养老模式的转变,探索一个有效的老年人社会监护服务体系,是解决当前老龄化问题的关键策略之一。
“意定监护”服务是伴随老龄化发展而来的新兴产物。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在提供意定监护服务的过程中,仍然面临服务标准不一、监管机制不完善、法律支持不足等诸多问题。
谁来为生死负责?
从上海驱车近200公里,在位于太湖边“江南名都”阳羡东部的王婆村,记者来到了当地唯一的一座养老院。
77岁的王柏龙(化名)是该养老院的一名住户。由于严重的糖尿病缠身,王柏龙已行动不便,一瘸一拐。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拿着一只不锈钢碗下楼打饭——一碗菜粥就是养老院当天供应晚餐的全部。虽然因疾病变得非常瘦弱,但王柏龙还是让人给他多盛了一口。
按照养老院的餐标,老人一天的伙食费约16元,绝大多数时间吃的是馒头和稀饭,王柏龙在这里度过了第四个年头。
王柏龙未婚无子女。几年前,他与同样未婚无子女的哥哥王立征(化名)居住了一辈子的祖宅被当地政府征收拆迁了,如今那里仅剩下一片废墟。村里的杨书记告诉记者,按照规划,王柏龙兄弟祖宅所在的片区即将被改建为科创园。杨书记承认,兄弟两人曾居住的房子分别有四五十平米,但他们并未得到分文拆迁费。
“别人拆迁政府会分配安置房,按照面积标准来分配,但他们(王柏龙兄弟)比较特殊,都属于无保护人群,拆迁费就变成集体财产,村里把他们安置在养老院,有病时带他们去看病,负责为他们养老送终,这当时也是征求过他们家里人意见的。”杨书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王柏龙在当地还有一个姐姐,但由于自身年龄也越来越大,无力再照顾弟弟。杨书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王柏龙没有正式的“监护人”。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对没有近亲属做监护人的群体,《民法典》规定由村居委会来做公职监护。具体而言,对农村“五保”之外的孤老、失独等身边无其他法定监护人或法定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的老年人,在其民事行为能力丧失或者欠缺时,根据《民法典》,民政部门或其住所地具备条件的居村委会将依法承担国家监护人职责。
但在与王柏龙的对话中,记者发现他的意识还是很清醒的,也未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他甚至还惦记着自己几千块钱的存款,希望将来能留给一个侄女。不过姐姐觉得王柏龙的头脑正在逐渐变得模糊。
谁来对王柏龙的生死负责?王柏龙自己也曾想过这个问题,但他没有答案。就在半年前,哥哥王立征去世了,两人生前虽然关系不怎么好,见面总是吵架,但哥哥的去世对王柏龙的心理是有不可磨灭的影响的。
王立征死于胃癌,在当地一家中医院经过了一个月的治疗后,他的病情恶化了。王立征去世的时候,王柏龙就睡在他的床边,他眼睁睁地看着ICU的管子还插在哥哥的嘴里,但人已经没了——在王立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医院把他从ICU运回了养老院,理由是“老人不能死在医院,会占用指标”。王立征死在了被运回养老院的路上,王柏龙抱着哥哥的尸体,失声痛哭。
村里人叫来殡葬服务公司的人,给王立征带来一套寿衣,那可能是他这辈子穿过的最体面的衣服了。两个人把他的头和脚一扛,塞进一辆面包车就送去火化了,骨灰就放在临时寄存处。王立征在乡土生长了一辈子,但“入土为安”这件事与他无关。
从哥哥命运的结局中,王柏龙仿佛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
“在农村,这样的孤寡老人比比皆是,这也暴露了社会养老的压力。很多没有子女或直系亲属缺乏照料的老人,被送到养老院后,很容易被欺负。”一位从事多年老龄工作的社区服务人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生了病如果不是起不来,不会有人带他们去看病,一到医院检查出来都是晚期重疾。”
10月13日,由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安宁疗护与医务社工研究中心、上海福寿园公益发展基金会,礼济学院主办的长三角一体化生命服务事业智库首届国际论坛举行。论坛发布《把“善终”带回现实:2024中国居民善终质量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善终质量的提升空间仍然较大,尤其是在提高临终患者生命最后阶段的生活质量和满足其心理需求方面。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实现真正的“善终”,不仅需要改善医疗服务和技术支持,还需要改变社会观念,加强对临终患者的心理支持。尤其是缺乏子女陪护的老人,更需要照料与心理关爱。
养老未必只能靠子女
居住在200公里外的上海,人们可能难以想象农村正在发生的一切。但少子化的趋势同样是现实,越来越多的人老去后,会面临“谁来为生死负责”的困境。
上海年近八旬的孙先生和孙太太的儿子移民国外多年。近期孙太太的认知能力下降严重,孙先生出于未来照顾和自身养老的考虑,与儿子商量后决定夫妻两人尽早入住养老机构,但在办理入住等相关手续时遇到没有监护人签字的问题。
几经周折,孙先生了解到现在有一些社会监护组织可以担任“意定监护人”,在找到某社会监护组织后,孙先生与该机构签署了意定监护协议,解决了养老院入住的问题。
费超是从事社会监护的民非组织尽善监护服务中心总干事。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像孙先生家庭的情况在上海并不少见。“上海有很多老夫妻条件都比较不错,但子女不在身边,也没有希望托付的亲属,遇事无人照料,住院也没有人签字,这种情况下委托我们进行监护服务的案例挺多的。”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尽善监护是全国成立的首个为老年人提供监护的社会公益组织,尽善监护于2020年8月在上海市闵行区成立,隶属民政局管理。费超表示,此类组织全国至今也仅有四五家,但都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我们是为老年人做监护的组织,至今确立监护服务关系的有35位长辈。”费超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有意识清醒的老人,也有些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老人,以意定监护为主,大部分的老人为养老机构的住户。”
所谓的“意定监护”,是指老人在意识清醒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意志指定监护人。目前,尽善监护拥有5名全职员工。他们日常的主要工作简单来说就是给服务的老人“跑腿”,例如领退休金之类。
费超介绍称,老人需要的服务在医疗场景下是最多的。从简单的日常探视、配药、陪诊,到住院、手术签字、抢救急救,再到老人过世的殡葬等身后事的操办,他自己就亲身经历了多个老人监护的案例。
费超向记者分享了两个较为深刻的案例。他至今记得自己在前年的一个大年夜突然接到闵行区中心医院的电话,他所服务的一个患有精神障碍的老人在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的途中去世了。在服务这位老人的三年半时间里,费超尽心尽力,保证一个月两次的探视,以及陪同就医等日常服务。
“虽然说我们服务这些老人不可能像他们的亲人对他们那样,但服务时间长了,还是会有感情。而且平时给予的是老人最需要的生活方面的协助,这也让我们有成就感。”费超说道。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并不是尽善所有服务的对象都是无子女的,也有子女关系不好或者长期不在身边的,比如孙先生夫妇的案例。“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提供服务可能是帮助老人度过他们最困难的时期。”费超表示。
曾有一对老夫妻因为与子女闹翻了,在卖房子时没人签字,于是找到了尽善监护,在服务这对夫妻的三年多时间里,费超曾参与了老先生两三次的急救,最后都转危为安,更值得庆幸的是,后来老夫妻与子女和好,结束了与尽善的监护服务关系,回归了家庭。
尽善监护服务的另一个群体为失独老人家庭。费超回忆称,曾有一个失独老人,生前在公证处留下一份遗嘱,希望尽善监护能在老人去世后帮助执行——具体内容是把老人生前的遗产平均分配给户口所在地的失独家庭。
“这个案例让我很感动,我们最后跑了大约100多户失独家庭,逐户走访,把钱交给他们,虽然不多,但完成了老人生前的遗愿。”费超说道。
“意定监护”为何难推动?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国家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第1款规定了“意定监护”制度,即:在老年人还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一位从事老龄化工作的民政机构人员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像尽善这样的组织的成立,是基于人口老龄化的宏观背景以及特殊老年群体的刚性需求而产生的,这也需要民政部门的支持。
公开信息显示,早在2020年12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负责人就曾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称,上海正在调研基础上,积极探索登记监护类社会组织。
不过,经过多年的发展,监护类社会组织在全国仍然只有凤毛麟角,民政部门在推动相关的意定监护工作方面也仍然遇到不少的挑战。
据费超介绍,尽善这类社会组织的收入来源由政府的采购项目、社会捐助构成,老人仅支付一部分公益性的成本。
费超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像尽善监护这样的纯公益社会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并不容易。“一方面是愿意无私奉献的人还不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老人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强。”他坦言,“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到这一队伍,同时也能让更多老年人了解意定监护组织的存在。”
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赵越凡也认为,意定监护的实现,能够充分尊重老年人的个人意愿,有利于弥补家庭监护的不足。但长期与老人接触过程中,她发现“监护”的相关知晓度很低。
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律师燕晓凤长期关注老年人的监护问题,她在过去一年走访了几十户失独老人家庭。她总是这样向别人介绍自己:“我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律师。”
她在走访失独家庭的过程中发现,超过九成的人不知道意定监护;在她去年执笔的《关于推进落实老年意定监护制度施行的建议》课题调研时发现,超过六成受访者不了解意定监护制度。
“由此可见,意定监护的普法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只有让更多的老年人知道意定监护,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燕晓凤表示。
在上海市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晓明也在积极推动上海意定监护的制度设计及具体操作规则流程等实施工作的落地。她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面访过的人当中,十个里面有九个都不清楚何为意定监护。”
“组织”监护人谁来监督?
虽然很多老年人有明显的社会监护需求,但其本身对于社会监护概念和社会监护组织的不了解,让他们不愿意轻易尝试社会监护服务;而当社会监护人承担监护业务的时候,医院、养老机构、银行、房产交易中心对于社会监护人(组织)资质的认可也是一大问题,这背后就需要政府公职部门的背书和监护组织的共同努力。
燕晓凤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民政部门对于包括失独老人在内的特殊老年群体的监护工作一直非常重视,民法典也有涉及意定监护的相关内容,但目前由于立法不够细化、健全,缺乏法律依据,导致相关方面的工作无法进一步落地实施。
在她看来,鼓励老年人运用“意定监护”制度为养老兜底,必须设计出不同主体相互制衡的机制,建立配套的监督保障制度,根据不同老人的需求,以及老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资源匹配情况,建立起以公职监护为主,意定监护为辅助的体系,并尽快完善登记备案制度,明确第三方的监督,廓清此行为可能给老人带来的安全风险。
“民法典虽然明确了‘组织’可以成为意定监护人,但目前监护监督环节仍不完善,仅依靠当事人间的意定监护协议可能无法更好地保障被监护人重大人身和财产利益,需要事前和事中的监督,新监督体系的建立和规则的完善等实践也需要有步骤地展开。”燕晓凤说道。
她还表示,意定监护相关监护细则仍需完善,明晰“意定监护”与财产继承、亲情道德等混淆模糊的领域。比如,意定监护人承担的监护职责与社会工作中的“照护”有显著区别。
刘晓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需求也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需要基本的生活照料,更需要心理慰藉和社会支持。”
在谈到意定监护在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时,刘晓明表示,意定监护组织的发展肯定应该给予鼓励,但此类组织的公信力有待加强。她也呼吁针对老年人意定监护中的困境和需求,推动实施细则尽快出台,同时鼓励更多爱心人士加入。
与意定监护在中国的发展相比,国外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意定监护服务起步更早,发展较为成熟。例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早在20世纪后期就开始实施意定监护制度,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框架和服务体系。在这些国家,意定监护服务不仅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范的操作流程,还有成熟的监管机制和质量控制体系。
例如在美国,社会监护组织1989年就已经被定性为一个新的行业。美国国家监护协会很早就已经制定了关于社会监护机构的道德准则和指导社会监护机构服务的标准。美国的《统一监护人和保护人法典》为意定监护提供了详细的法律指导,确保被监护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第一财经记者曾经采访过长居在美国的刘新宪,他原本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高层。他家庭经济条件很不错,职场前景一片光明,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然而多年前,孩子的骤然离世让刘新宪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当时他内心所承受的悲伤和压力难以言表,最后他辞去了高薪工作,让自己缓和了一段时间。作为一名失独父亲,刘新宪一度很痛苦,他也并未再育,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他现在成为了一名哀伤咨询师。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接触到了哀伤咨询和心理疗愈,我了解到有不少欧美国家的人从40多岁就开始写遗嘱以及安排一些器官捐赠、临终治疗的事宜,这样就不会到时候手忙脚乱,在美国有很多家庭都有家庭医生,他们会有一套完整的生前事业手册,包括需不需要抢救、器官捐赠这类,他们并不忌讳,而是通过系统化和产业化的方式来做成了一套生命事业体系。”刘新宪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
就在日前,第一财经记者再度回访刘新宪,他表示自己目前生活很稳定,心情也早已平复,对于养老问题,他选择找一个指定(意定)监护人,写好生前预嘱,对于是否要抢救等作出决定,并且将财产也做一定的分配,包括给指定(意定)监护人具体如何分配等。作为监管,可以由相关的律师、机构或者指定两个、多个指定(意定)监护人来互相监督,以确定自己万一失智后的照料保障。
此外,一些国家还通过专业的监护人培训和认证制度,确保监护人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于2000年前后就开始为社会监护人建立法律制度。燕晓凤建议,可以参照日本的“职业后见人”制度,在我国建立职业监护人制度,包括建立职业监护人培训和资格认定机制、明确职业监护人的种类与职能、建立职业监护人监督机制。
无论如何,这种新的监护制度的探索为未来的养老模式打开了一扇新的窗,也能让更多无监护的老人在人生最后的旅程中,多一条选择的路径。
转载请注明来自共享纸巾,本文标题:《老有所依|谁来为“无监护”老人的生死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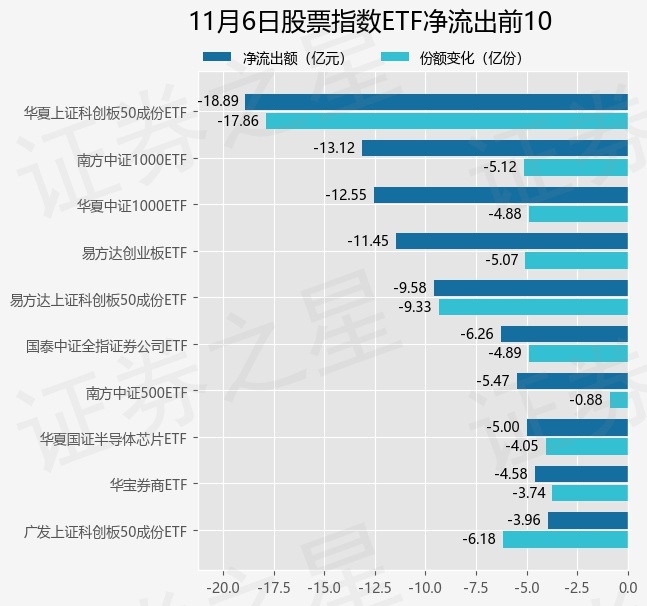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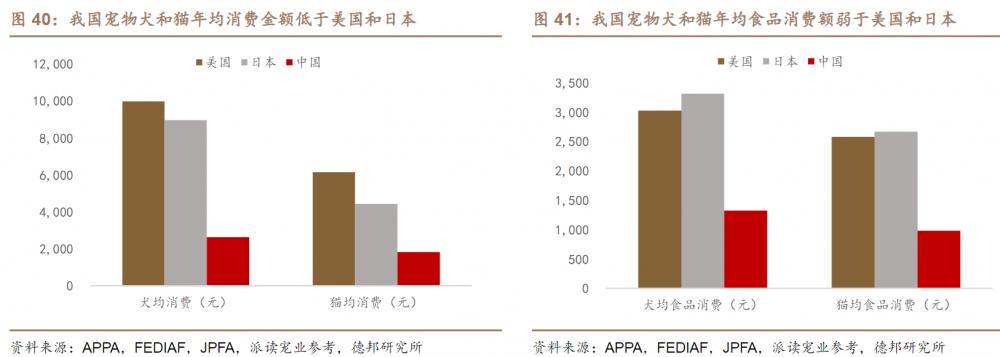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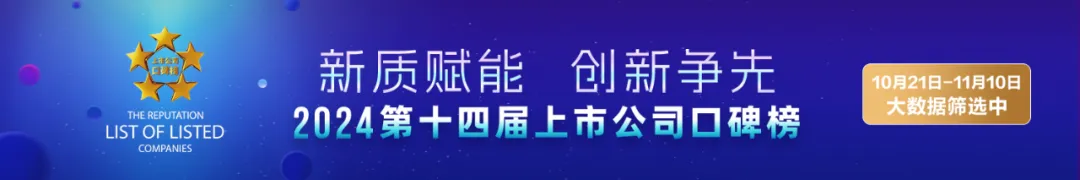

 闽ICP备19021180号-2
闽ICP备19021180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