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弗
那一年,我十六,他十九。
在学堂的朗朗书声中,我曾见过他妙年洁白的身形。他,是我父亲的得意门生。
而如今,我该唤他一声“郎君”。
他喜欢在朝云初起时眺望天际,喜欢在昏昏灯烛中抚卷沉吟。家中书房虽然窄小,我总赖在他旁边,光是看他时而摇头晃脑时而眉目耸动,就有无穷的趣味。
有时他背书卡住了,我便轻轻提醒,倒惹得他大为惊诧。他在书架前上蹿下跳,试图把我考住,终究未能得逞。
从此,他看向我的眼神,似乎比从前,更多了几分光泽。
人们都说,丈夫志四海,可我觉得,外面的世界,他并不适合。
是的,他红了,有个叫欧阳修的先生说,要放他“出人头地”。就连当朝皇帝,都把他和子由,当做宰相来培养。
可是,他又哪里知道人性幽微,官场混沌呢。
每次开门纳客,他总是满心欢喜,觉得又交到了一位知己。可我躲在屏风后听到的,根本不是这样。
我和他说:今天来了个“阿谀奉承怪”,你怎么说话他都顺着你,还来了个“称兄道弟怪”,一日千里地自来熟,两个人都不是你真正的朋友。
起初他不以为然,他以为自己掏心掏肺,别人自然输肝剖胆。但后来发生的事,让他不得不挠着头腆着脸,来向我认输。
真是傻得可爱。
书读多了的人,脑子里常惦记些有的没的。一年冬天,大雪满山,四望皎然,庭院中有一小块地与众不同,不但不积雪,天晴后还微微隆起。他大喜过望:“此地必是古人埋藏丹药处!”
我摁住了他手中的铁锹:“若是婆婆尚在,必不许你如此迷惑颠倒!”他便乖乖收手。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和子由渑池怀旧》)
十一年时光,像受伤的飞鸿,缓慢,但终于飞远。
二十七岁那年,我卧床不起。他的双手在我的手上几乎攥出血来,却被病魔一指一指掰开。
他把我葬在明月夜,短松冈,八步开外,就是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婆婆。
逶迤的山岭间,挤满了他亲手种下的三万株松树。
我是喜欢松树,但三万株,未免太多。
可惜这一次,我无力劝阻。
二、王闰之
他曾是我的堂姐夫。
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称我为“妻子”。
堂姐留下一个儿子,我又为他生了两个。在所有人眼里,我不如堂姐蕙心纨质,一生最大的成就,或许便是让这个家更有家的感觉,家的温度吧。
在少女时代的绮丽幻梦中,他曾是最为闪光的存在。他的清词丽句,他的趣闻轶事,甚至他那些深奥的家国天下,都被我抓着闺蜜聊到她想逃。
有句话说得好,千万不要嫁给自己的偶像。更何况,我赶上的,是他一生中最为动荡的岁月。
京城里搞变法,闹哄哄,似乎他不怎样赞同。吃饭带娃时,他也曾向我抱怨过的,可我又哪里搞得懂?
他便把那些牢骚,都写到了诗文里。而这,几乎要了他的命。
最早在杭州,就有个叫沈括的家伙(都说他写过一本十分厉害的书叫什么《梦溪笔谈》),来和他谈诗论文。谈完带走一册新诗,称要好好拜读。
一转头,这本新诗集,做了详细的笺注,被当成诽谤朝廷、攻击新法的罪证,呈送至神宗皇帝御前。
那一回,他涉险过关了。但地狱之门,已悄然开启。
在湖州的山光水色中还没坐热屁股,他便被抓到了京城的大牢里,因为同样的指控。
众目睽睽之下,顷刻之间,捉一太守,如驱犬鸡。而他居然回过头来嬉皮笑脸:“走啦走啦,这种时候,你就不能写首诗,送送我?”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轻松是装出来的。若不是吏卒看守严紧,他已在扬子江边投水自尽了。
梦绕云山,魂飞汤火,御史台大狱暗无天日,他熬满了一百三十天。而我,带着全家二十几口人,远涉江湖,灰头土脸,去投奔子由。
半路上,大批官兵围住我们小小的船,凶神恶煞,翻箱倒柜。我不禁悲从中来:“好好的过日子,非要写诗!我这是受的什么罪呀!”
一气之下,他残留的诗文手稿被我付之一炬。那天夜里,我仿佛看见他沉默着来到我梦中,龇牙咧嘴,一脸肉痛。
囹圄深深,霜气袭人,诟辱通宵,“咬”文“嚼”字。所幸,硕大的漩涡虽不怜悯蝼蚁,岸上总还是有几人伸出希望的枯枝。
他在狱中,不止一次想要自我了断,甚至写了两首绝命诗,但终于大难不死,远谪蛮荒,一家人重又在黄州团聚。
突然的苦难,让他迅速长成一个精神的巨人。就连子由都“酸溜溜”地说,从前他们兄弟二人,诗文原本不相上下,自从黄州之贬,他便一骑绝尘了。
让我尤其欣喜的,是他终于学会了收拢掉毛的翅膀,从云端降落到地面。从前的他,俸入所得,随手花光光。说他两句,他便搬出李太白的诗句——“千金散尽还复来”,明日自有明日财。
这下好了,他竟摇身一变,成为节约的能手。经过精密的演算,他认为一天的花费须得控制在一百五十钱以内。每个月初便提前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为三十份,挂在头顶的房梁上。每日清晨他用叉子叉下一份,然后,将叉子小心藏起来。
我知道,世人眼中的他,乐观旷达,永远以强韧的身姿、倔强的面容,站在人生困境的对面。闾巷争传“一蓑烟雨任平生”,学童书册写满“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样的他,的确浑身发光,让许多人从中汲取了坚持的可能、前行的力量。但也正因如此,人们常常忘了,他不过也是血肉之躯。当被命运绊倒在地时,他也会难过得像个孩子。
黄州四年,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为猪肉作颂,在命运的深渊里,依然是个无可救药的吃货。殊不知,他也自闭过,颓唐过,羞于白日出门,甚至不敢和朋友联络。
从“嗟余潦倒无归日”到“畏人默坐成痴钝”,从“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到“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他笔下的酸楚并不比旷达少,人们却常常只记住了后者。
而更让他忧心如焚的,是四海鼎沸,民生日蹙。变法让朝廷府库日益充盈,百姓的面容却一天天干瘪下去。
也许我该庆幸,在漫长的泥泞过后,终究有一段坦途在黎明等待着。说起来似乎不厚道,但神宗的英年早逝,的确让他得以东山再起。
短短一年,他扶摇直上,玉堂金马,荣宠一时。在倥偬的案牍与潮水的宾客中,他的笑容温暖,嘹亮。
他素来喜欢命俦啸侣,但以今时今日的地位,家中难免奔走竞进之徒。每次来了这样的俗客,他便大张旗鼓摆出歌儿舞女,在衣香鬓影与急管繁弦中,竟和来人终席不交一谈。
我知道,他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只不过披上了华丽的衣冠。
变法暂时坠入了低谷,但朝堂之上不无隐忧。司马光矫枉过正,要把所有新法一概废除。
在他看来,就事论事,有些新法还是值得拥有。可当他挺身而出提出反对意见,大家都感到不能理解。他不是被变法派迫害最惨的那个吗?尽情享受大仇得报的感觉不好么?
他和司马光大吵一架,还帮对方改了个名字,叫“司马牛”。
“司马牛”没来得及向他露出獠牙,就撒手人寰了。但他不肯圆融藏锋,终究不是长生久视之道。
我不知道隐秘的风暴会在哪个角落聚集,在他人生最灿烂的时刻,我终于病倒,离他而去。
我曾陪他走夜路,蹈泥涂,戴皇冠,听欢呼。尽管,“冰姿玉骨”不是我,“不思量自难忘”也不是我,但,冢中枯骨两相依是我,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是我。
也许我没能握住他的灵魂,但,能在沧桑的九年等待后,终于和他并肩躺在漆黑坟墓里,也不失为一种枯燥的浪漫吧。
三、王朝云
不知为什么,他爱的人,都姓王。
我不过是他的如夫人,却凭着一句“不合时宜”的吐槽,被人们深深记住。
初入苏府时,我懵懂无知,飘零日久。新生活里的全部色彩,都来自他的馈赠。
他大我二十六岁,但我仿佛从他出生,便已和他朝夕相处。他的世界充满明枪暗箭,而我尽力让层层叠叠的伤口,开出明媚小花。
天长地远魂飞苦,人生乐在相知心。
他什么都好,就是不该含情脉脉,叫我“老云”(王闰之:我插一句,他也总叫我“老妻”!)。
我有时觉得,他待人接物极为成功,即便身在困厄,仍能凝聚许多性情中人。他们千里万里,也要赶来投奔。
有时又觉得,不知他在搞什么,连他倾心教导的学生,居然都会恨他入骨,嘴里时常恶狠狠念着他的名字。而这个后来把他贬得七荤八素的学生,就是神宗的儿子——哲宗。
在一般人眼里,歌姬侍婢不过是富贵生涯的点缀。在他飞黄腾达的岁月,他有过好几个和我一般的侍婢。
等到他花光好运一落千丈,便只剩我一人,愿意陪他远历遐荒,苦度年华。
我们有过一个珍贵的孩儿,他还写下一首流播千古的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洗儿诗》)
只可恨,我们的孩儿,只活了不到一年,便被病魔摄去。从那之后,我的身体每况愈下。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在惠州的仓皇天空下,他让我唱一唱这首《蝶恋花·春景》。而我被这两句卡住了喉咙,催湿了眼睛。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命运不正像那个隔墙语笑的佳人么?多少人用尽一生逾墙折杞,终究不过枉自多情。
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
(《朝云诗》)
在佛经与药炉中间,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衰朽,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四岁。
而他,终生不再听那首《蝶恋花·春景》。
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
(《悼朝云》)
他葬我于栖禅寺大圣塔下,害我的魂魄夜夜辛劳,衣衫尽湿地渡湖回家。后来,他便在湖上建构长堤,遍植腊梅。从松树到腊梅,他讨好女孩子的手段,如此单一。
也许大兴土木,能够缓解他心中伤痛吧。临终前,我反复念诵《金刚经》中的偈子: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他便为我筑起一座“六如亭”。这做法或许浮夸,但我喜欢他亲笔书写的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庭户无声,明月窥人的夜晚,也曾起来携素手。
春风春雨,彩蝶双栖的时节,也曾起舞在人间。
纵然这一世烟柳断肠,落红无数,毕竟曾有人和我冷暖相依。
浮云流水,他生缘会,就让我们翘足期待,下一个轮回的相遇。
本文原刊于《北京文学》,经作者授权转载
本文作者,彭敏,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中国成语大会总冠军。
《曾许人间第一流:古代诗人骚客的激荡人生》是彭敏首部以诗词为主题的作品。
从陶渊明、李白、王维、杜甫,到白居易、苏轼、李清照、陆游…… 彭敏带我们领略29位古代诗人们的诗酒江湖与慷慨人生, 直面他们的 人生困境,体认他们的 诗和远方,还原他们的 率真可爱。
这本书帮我们撕下诗人们的刻板标签,让我们看到他们丰富、多元、灿烂的一生
《曾许人间第一流:古代诗人骚客的激荡人生》作者: 彭敏出版社: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品方: 捧读文化出版年: 2022-7
转载请注明来自共享纸巾,本文标题:《嫁给苏轼,是种什么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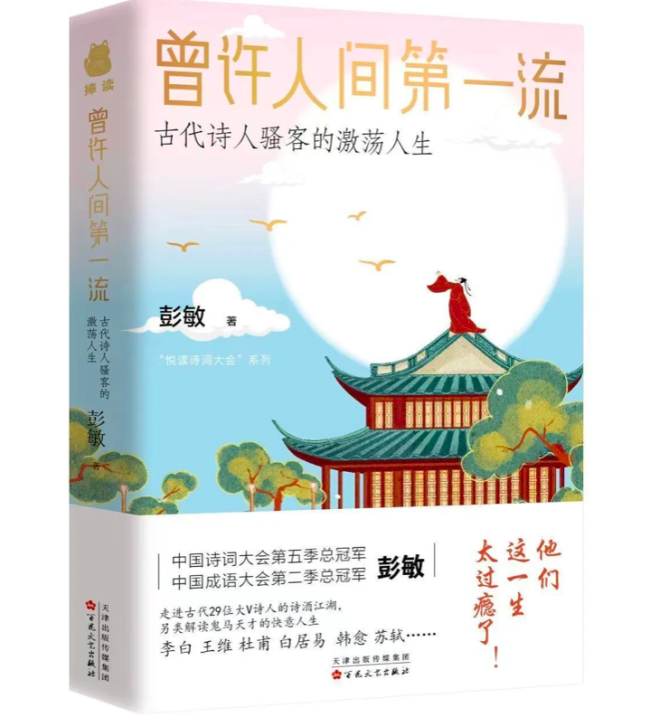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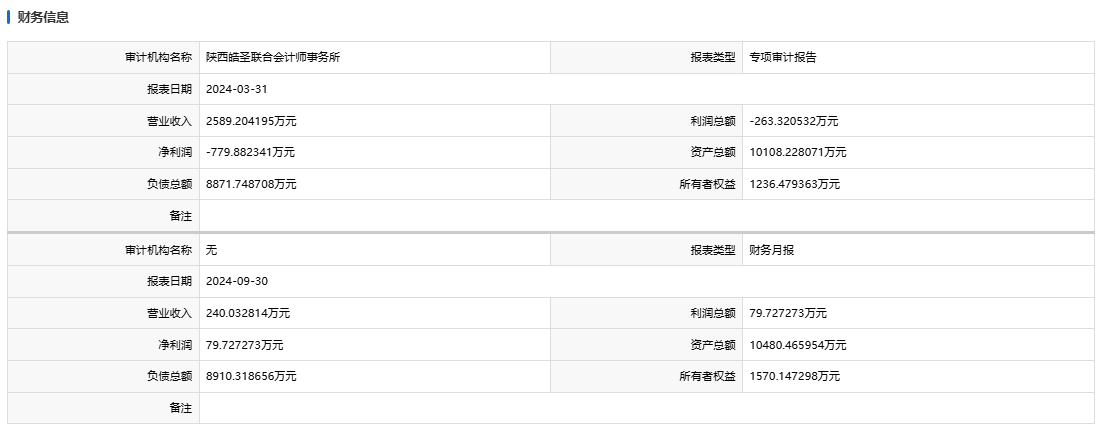





 闽ICP备19021180号-2
闽ICP备19021180号-2